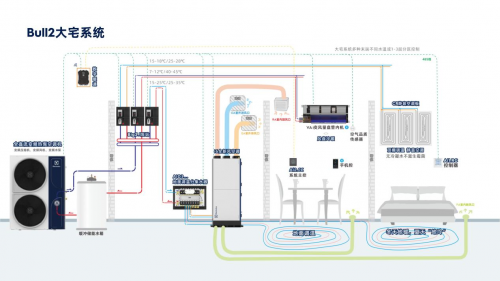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一大早起来,雾霭蒙蒙间骤见依旧郁葱的树下吹落一地枯叶,看着不是金黄自落的感觉,而树间的绿叶依稀开始泛黄。骤然间才发现,原来2024年的时间轴距已不知不觉间拉至仲秋之际,而且距离团圆的中秋节都只剩下短短的一个星期了。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今年的秋雨好像格外的多,飘飘洒洒、滴滴答答、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对于旱了整整一个春夏的陕北而言大家并不感慨怡情,有的只是对雨落大地时机不对的抱怨,尤其是靠天吃饭的农民,用他们的话讲“这雨下个没完没了,好像不好钱似的尽管倒了!”几十年不见的陕北大旱让山间的庄稼收成可谓是惨淡至极。
我想如果外婆还在的话,中秋我们回去肯定也得絮絮叨叨地抱怨“天道不行”。
睹物思人,触景生情。外婆已经走了差不多五个月了,一直想写一些关于外婆的事,但是心中的怀念和工作中不断地忙碌不知道从何下笔,恰逢中秋之际,团圆之时,终于鼓起勇气提起了笔,用于缅怀,也用于面对。

外婆是今年农历三月初十跌了一跤不省人事的,在这不省人事期间的两天中她见完了远在外地赶回来的所有子孙后辈,三月十二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能要强的她感觉所有的亲人都见着了,心愿也了了,才舍得离开我们。
外婆走得很突然,让我们连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就再也没能和她拉两句家常。虽然外婆已经是83岁的高龄,近年来身体一直欠佳,每年都得住上一个月院,家里人都有心理准备,但是这么突然的离去仍旧是所有人不能接受的。犹记得去年去医院看她时还对我问长问短的,“单位工作忙不忙?回来待几天?”“那两个龟孙子上学了吗?爱不爱学习呢?”……现在想起来外婆的声音还犹如昨天般在耳边回荡。
那时候接到母亲告知外婆跌跤的电话时哽咽的声音都是颤抖的,眼泪止不住地在滚落,但还得安慰母亲不要过度悲伤,因为我知道他言语中的“人老人了生老病死正常,你外婆年龄大了,走的这么突然是不想拖累儿女,她自己也少受点罪。”是在自我安慰,她和外婆一样要强的外表和言语下的安慰都是极致悲伤的表现。
外婆一生要强,又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人,和外爷都是八十几的高龄了仍旧不愿意上榆林来和儿女们一块生活,可能在她的理念她自己还能动,和外爷相互照顾着还能行,不能上去拖累儿女们。而且待在老家还能给儿女们种点瓜果蔬菜、豇豆、绿豆啥的。用外婆的话说,“她也有自己的‘日月’了,她要不在老家这些窑洞、地都得撂!”

外婆的葬礼上,我们后辈子孙在布置灵棚、客棚及吹手场地的时候,脑畔上、碱畔上所有能种的地里韭菜、瓜苗、豆角辣子等都刚露出了头,狗窝边上的石板上她放的泡沫箱子、纸箱子里种的五花八门的幼苗也均已露头。母亲在那念叨,“这‘老家’还准备好好过她的日子了,各式各样的瓜果蔬菜他都在育苗,不知道在贪饕啥了。还不知道要给儿女干出来点啥成绩了!”说完就止不住地抹眼泪。
外婆从不省人事到去世、出殡一共9天,母亲就整整哭了9天。有时候在收拾东西的时候见物伤怀,有时候来了亲戚时悲从中来。从母亲的言语中我体会到了她遗憾揪心的是外婆没能给她交代一言一语的遗言就走了,常常忙碌的她都没能好好伺候外婆几天就这么不声不响地走了;她悲伤的是她从今往后回老家的路上再也没有人给她打电话问她吃什么饭,也没有人再给她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老家来了。也再也没有人给她诉苦说这也坏了、那也坏了……
外婆从30几岁的时候就一直病痛缠身,用药物维持,在我的印象里她那腰就没有挺直过,一直是弯着的。但是就是这弯着的腰却将我从出生背到7岁。因为母亲和父亲是一个村的人,那时候父亲在外务工,母亲从山里种地回来一般都是在外婆家吃点饭才回家,有时候我们睡着了都是外婆背着送回去的,那时候一直没有感觉到外婆的腰是弯的。外婆出殡那天,我趴在棺材上看了外婆最后一眼,她的容颜比她在世的时候都要好,可能没有痛觉了,她那一直挺不直、睡不平的腰终于是平平直直的了。

外婆走了,没有把她视如珍宝的铺铺盖盖、锅碗瓢盆进行分配,也没有一句离别的话语就走了,用家乡长辈的话说,这样也好,有想有念!
外婆走了,不是在寒冬,而是走在最美的四月天,可能她也感觉走在初春的路上,一路上的花花草草可以吹淡离别的伤感吧!
外婆走了,往后回家和离家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站在山峁峁上给我挥手了,再也没有人叮嘱我“不要喝酒、开车慢点”的絮絮叨叨了!
外婆走了,忽然发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少了一个最重要的容身之所,从此烟雨洒青山,故乡暂无家!(贺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