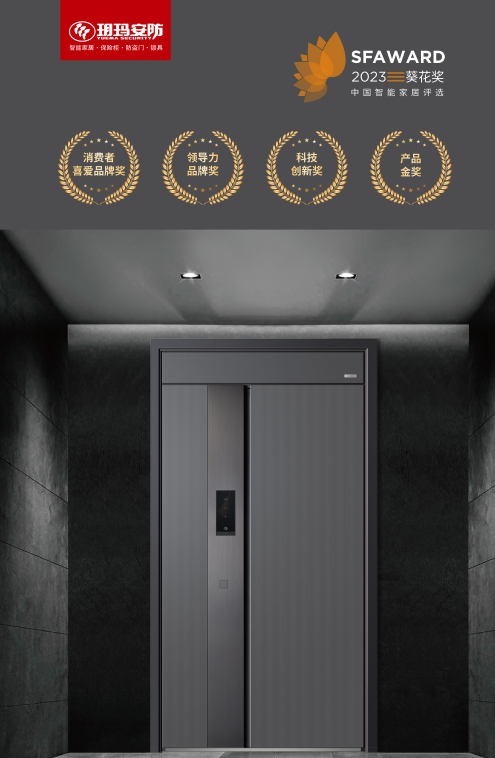一,山水之光 —《杨多对话张春旸》
想写一篇山水精神与山水之光有关的文章。就像孔子写讲的:智者爱山,仁者爱水。我理解这不完全是说智者去喜爱山水,而是山水能培养出人的品质。就像我特别喜欢王阳明的心学,人在不断格物、不断地致良知过程中,在自我的心性中强大,超越自我,这是人的伟大之处。如同人在宗教情中所要焕发的出精神吧。就是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跳出自我的情绪感受,获得一种光芒的为人品格。从山水的品质里面与心性的开阔里,寻找到了一些可贵之处。这是我在这批风景画里体悟到的收获,也是我画风景的内在需求。面对自己,如何用熟悉的的油画形式,画出我个人不一样的理解。同时,我在大理的地理环境中体验到一种具体的金色的光,像人性里的一种光芒!绚烂、灿烂与温暖,对我是一种指引。如何将这种对光的向往指引内心,以一种更博大的情怀与之共存?与其说这批风景画是对自我的挑战,对更加完备自我的向往,对自我的修炼等等。应更贴切的描述为:尝试不断地超越自己,超越现有的情感与人的状态。就像我以前是追着光芒跑,直到光芒驻足心里。在心中有饱满的光明的状态,这是我从山水中获取的品质:一个画家从自我的困惑与迷茫到与自我的和解,都是在寻找一种近乎宗教情感的品质。在获得这种情感之后,能够将它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地回到生活的原点。用这样一种更广泛的人类情感,包容了以往的曾经的所有。这种宽容的感受就像水一样,具有无限包容性;而山的笃定、雄壮与坚韧,可能是在绘画中培育出来的或者提炼出来的,焕发个性中最坚韧的一面。乐山与乐水,遂山与水的品质连同阳光炙热的照射进我内心。感叹天地间同一个太阳,这接近赤道带的阳光曾经给予艺术大师们的慰藉,在我的这批作品中也能找到。

我曾把中国的古典山水画和西方的印象派之后的绘画建立了一个比较关系,通过比较中国绘画的章法与西方印象派之后的绘画语言,如何以绘画元素来构成绘画的共通关系。比如,线条作为一种绘画元素而存在,色彩凸显出来成为更加纯粹的色彩。色彩和线条构造一种对空间意识的理解,绘画语言的内在逻辑像中国绘画的章法构成。这种知觉心理的感受从属既定的范式,比如开合,疏密,曲直等许多相对的元素来构成空间关系。那么我理解到的印象派之后的西方绘画,就是线条与色彩都相对突出出来,空间关系也区别于以往西方油画光线的理解。把人的因素融入进来,人在绘画中游走穿行。在一个更为广袤的空间里,人是很小的,在与天地相契合的大道中,人的情感是低微的。如何在山水画中追求开阔的大山大水的视觉精神?中国山水画中产生了一种纯粹的水墨,其实黑白就是一种光,应该被更贴切地描述为一种心性的光明。不是寻求外在的光影的变化,而是引申到人的心理层面去导引出光的存在。中国绘画里一直在讲人的修养,如石涛的“一画论”,一笔就能画出人的修养。这里面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所理解的绘画里生成的智慧就像光芒一样,把光引入心里,然后这个光从内心中不断地散发出来,我以一种比较抽象的方式来解释中国古典绘画对的光的理解。就像一个人的自我修养,自我不断地提升,不断地修为,不断地像圣人一样去引导自己的心性。这些修为其实都是对光的精神内化,人格中的光芒才从绘画中被带出来。一个人绘画里存在的这种绘画语言关系,其实和他的个性与一生的经历有关,画里的光是个人人性光芒的延伸。比较中西画中对空间关系的理解,如何在人心的光芒里表达对空间关系的独到的理解。

就我个人的绘画来说。来到大理之后,结束了马语系列。马其实是我对宗教情感的追求,对自身不具备的心理上的向往,而后我迫切希望回到现实生活中。居住在大理喜爱亲近自然,常常爬山,每每站在苍山上眺望洱海,如同攀登与攀越就是我的修行。所以近一年半,都在画风景里的光,画上山的路,就像不断地引导自己,走到那种光明中。于是我的绘画里出现了一些比较硬朗的一面,在山水与光明的描述里中,可以说我重新塑造了自己。让我的品质与性格变得更加浓重与厚重,也更加简单了;这些绘画让我对光明的追求更加迫切,充满了希冀与向往。我感觉自己的生命的热情也由此被点燃了,生命变得更饱满。就像王阳明说的人性的光明,我把光注到了我的心里。其实我的绘画里的山水就是我 的生活指引。我在画风景画时,常常想象塞尚晚年在画圣威克多山时候的情景,他通过简单的色彩,在晚年的绘画中营造出的那种光。我觉得人性的光芒与绘画中的外在的光是同质的。一个人的个性与绘画语言完全融为一体。绘画是对自我情绪的一种安抚同时对自我的指引。我在这些风景画所追寻的,其实和这些大师所做的一样,我把我的心性通过山水画培育出来。我在绘画的过程中,修行与不断地度化自我,在山水画中我又超脱了自我,进入山水-自然-大道这一中国传统的山水精神的命题,由此遵循生命个体体悟的绘画语言应该不分中西。所以,我感觉山水之光是这批风景画所要表达的主题吧。
二,从表现到抒情:张春旸的诗意表现主义风景画
2014年,在已故艺术评论家黄专的策划下,张春旸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做了第二次个人展览“马语”。对于春旸,策展人做了如是定义——“当代中国少有的坚持以表现主义进行创造的女性艺术家之一”。在黄专看来,春旸的创作始终围绕着个人世界这一主题,“马语”即是这一气质的继续体现,更为重要是的是,这一系列所蕴含的“宗教意涵几乎与乌托邦式的田园意象同样清晰,与2011年第一次个展‘爰笑爰语’时期的作品中神经质的人物造型不同,‘马语’带有童话般的意象”,策展人宣示“急促紧张的笔触和强烈的色彩反差溶解在透明的淡彩之中似乎是一种完成世俗救赎后的静穆,生命因为寻找到了某种本真含义而轮回到了它的起点。这种意境不再与孤寂、痛苦和阴郁相关,而与一种超度性的诗意幻象相关,对于根植于现代人类焦虑本性中的表现主义艺术而言,这是另一种逃离现实的梦呓方式呢,还是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谱系的诞生?”

或许是艺术评论家的洞见,抑或是评论家的声音在艺术家的心里留下了印记,春旸在个展结束之后的 2015 年,离开了居住了十几年的艺术中心北京,南下寓居洱海之畔的云南大理。春旸的南下,也许与当时的城市化高压下理想化为泡影的年轻人逃离北上广“一路向南”寻找诗意南方的民谣运动相合拍,正如评论家管郁达所言,这是寻找“灵魂逃跑的一个出口”。
在艺术史上,不少艺术家在盛年选择离开艺术中心寻找新的议题,例如罗申伯格(Rauschenberg)逃离纽约中心的喧嚣,在迈阿密海滩小镇获得边缘视角的突破。离开巴黎的梭罗(Henry Thoreau)在瓦尔登湖发现了自然中花草的美好,南加州的艳阳与好莱坞的泳池造就了标志性的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在大理,春旸说她发现了“光”,人物第一次不再是她画作的主题,进入了她的风景画时期。大理的“风花雪月”与苍山之麓的美景,似乎是春旸转入风景画的必然选择。而事实上,春旸的风景画创作可以追述到2004年毕业后在中央美院第六画室任教期间。2007年带领央美学生至山西平遥写生实习时,风景已经进入春旸的视野,创作几幅记录式的油画与水彩风景作品,如《来过这里》,《小教堂》等。在随后的具有田园牧歌与象征主义风格的“马儿”系列中(即“马语”系列的展览主体),叙事的背景已经由“我的样子”时期(图片)内心意象世界转换到田园牧歌的山谷海岸,草场与河岸。来到大理之后,当苍山洱海取代了北京纷繁复杂的艺术活动,高原烈日,红色土壤,风花雪月,边地人文与新奇土产,新知与旅人的好奇替代了禁锢于都市艺术圈中自我之战,春旸的创作走出了自我的故事,不再专注于人物的描绘与剖析,开始由感悟与感叹转向记录与抒情,风景画这一帮助塞尚确立绘画现代性的绘画类型(genre),在春旸的手中,“风景画不在是绘画类型成为了媒介(medium)”。

在现代艺术史上,风景画与印象主义有着最深的关联,在捕捉记录自然中的光色的无穷变化中,莫奈开启以再现视觉经验为艺术要旨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则是在反对印象派固执于视觉客观性的描绘中诞生,要用视觉艺术像尼采一样追问何为自我。作为表现主义艺术家代表的春旸,在云南开始思考如何在风景画的现代性话语融入进表现主义手法。在春旸的《彼岸使人心清空》中,观者不难察觉可以看到印象派的影子。在绿茵丛树之中,沉静于阅读之中的少年与怡然自得磨痒的黑色小犬,绿色与黑色的对比,让观者自然而然联想起宣告了印象派诞生的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不过,春旸并没有像马奈那样特意营造舞台效果,以人物社会与心理关系的叙事构建画面意义,而是以莫奈式的即景拍摄手法记录了日常的恬淡瞬间。画面左侧道路构成的对角线构图将观看的视角由画面前景直接拉入画面的深处,观者的目光留意到背景处树林间的纵向光线,而地面上层层的水平平行光线与前景人物旁的草地上的光点形成呼应。这里,光线取代人物成了画面的精神主题,引发观者通感的体验。

大理、丽江与凤凰是2010年代文青逃离过度商业化的都市寻找田园诗意的精神圣地,而逃离旅游催生的酒吧、咖啡馆及各类画廊却有趣地让古城成为披着田园外衣的嘉年华游乐场,大理汇聚了一批各地的艺术家们,春旸常常参与当地的艺术聚会,但热闹与人事都没有进入画面,画里出现的只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大理城外洱海边的陶潜式隐逸幽静。春旸的画不在关注画家的自我,不在是他人之间的社会性以及心理的剖析者,设置隐去了2000年代时期作品中明显的女性主义色彩,走向表现单纯而普罗的心理情感。
春旸在大理创作的风景画中不少具有写生的即景感,城外的苍山玉带路,黑龙溪,龙龛码头,大理财校的上山之路,真山真水的实景第一次出现在了春旸的作品中,作品的标题也往往采用地名而非此前的诗意寓言。在这些作品中,春旸以简洁而略带几何感的笔触描绘日常所见所感的景与物,《半入江风半入云》中蓝色湖面上惊起的白鸥,《风俗淳》里不经意路过的白墙黑瓦的白族民居,《上山的路系列》中山路旁林间松针上的阳光,《才村码头》不期而遇的洱海湖面上的天光。这些充满偶然性的取景构图似乎就是印象派画家的写生,表现画家即刻的感受,不过在用笔与用色上并没有走向印象派的细碎,而是用蒙克式的洗练而概括的色彩与用笔。在这些系列作品里,春旸似乎已经摒弃了北京时期“我”的系列题材的隐喻叙述,人物之间谜一般的画面关系。“你的样子的”人物画中的对自我的关照转而为对风景间的体验。像作曲家以音色书写旋律一样,春旸运用几何感的色块构型,以略带象征性的补色色彩来带动观者的共鸣与移情。观看由过去的猜谜变为体悟。画面不仅仅通向他者世界的一扇窗,而是像是宋元时期的山水,艺术家邀请观者进入的画家创造的你我之境,产生了此时此景的即时感(immediacy)。评论家陶咏白注意到,春旸画中各式各样的“路成了这批作品的生命主角”,从这些由画幅边缘切入画面的路面,观者引领进入画家的世界。

当然,春旸也没有完全放弃“马语”系列的隐喻与寓言,人物以及象征的符号还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是画家留给观者解开画面隐喻的密钥,《密林深处神灵的启示》中,位于画面中心线上草丛里写着藏密符号的玛尼石,与远景地平线构成对角斜线上的白舟上似乎已经启程,而湖面上几笔深色的波线是倒影或是牵绊航行的纤绳?在超大尺幅的《定风波》中,画家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落日之景。在一自然之景中,观者的凝视聚焦于画面下方几乎位于画面中轴线上的湖石及其上面贴着的藏密经幡,然而震慑于满天壮阔的彩霞,叹谓自然的奇伟,对于人迹与自然的冲突,关于经幡的寓意,观者却进入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物我两忘之境,寓意消弭在湖光山色的诗境之中。这种抒情延续到春旸由大理回归北京之后做了些许的变化,在纪念碑式的大幅作品中增加了挑动情绪定动势张力。在《通达》中,张春旸以留白和薄薄的冷色调交代出虚空,公园一角的冬日树木向上舒展延伸的树枝舞蹈般向上延展,仿佛有了马蒂斯舞蹈的姿态。

风景画是西方现代主义以来最重要的画科,但在春旸笔下,风景画成了抒情的媒介,通过风景与树林,春旸以印象主义的即时感与日常驱逐了过去作品中表现主义的神秘与隐喻,以表现主义的象征性色彩与构型来完成中国田园诗歌的抒情笔调,以中国抒情传统对抗印象主义的客观写实,将表现主义的色彩与线条提调为中国绘画美学的无声之诗,完成了从早期执着于个人世界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到体物忘我寻求“天地之间人类共同情感的绘画大道”的抒情主义的转换,从而完成了多年以来已经在不断实践的“诗意表现主义”绘画的建构。在张春旸看来,“这就是黄专老师所说的预示一种新的美学谱系的诞生吧。”
张春旸简历:
2004—2009年 受聘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于第⼆⼯作室与第四⼯作室任教。 2015年 受聘于中国⽂化部艺术发展中⼼中国书画院名誉院⻓。 2016年 推出 “⾏⾛的画室”。 2019年 推出 “⾏动⼯作室”,介⼊公共艺术领域。 她的创作谨守表现主义内在化精神救赎的美学遗产,始终将 “个⼈世界” 视为艺术表现唯⼀重要的主体,依托 强烈的感性直觉和⼴阔想象性的神性的⽣命体验,以诗性思维的神秘性提出 “诗性表现主义。
个人画展 :
2019年 “换了⼈间—张春旸作品展“,昆明当代美术馆,昆明 ;
2014年 “⻢语:张春旸个展”,今⽇美术馆,北京 ;
2011年 “爰笑爰语—张春旸作品展”,何⾹凝美术馆,深圳 ;
2008年 “你的样⼦—张春旸作品展”,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北京 ;
2006年 “你在⾥⾯”,四合苑画廊,北京 。
联合画展:
2023年 “在林中路上:OCAT十八周年典藏展”OCAT当代艺术中⼼,深圳;
2021年 “山海之约”康佳集团公共艺术项目 何香凝美术馆 深圳;
2021年 “奇妙的旅⾏—献给孩⼦的艺术展”,OCAT当代艺术中⼼,深圳 ;
2020年 “绘画的逻辑”,⽯家庄美术馆,⽯家庄 ;
2020年 “苗朵向阳开”,华侨城北⽅集团公共艺术项⽬ 七九八 悦美术馆 北京 ;
2020年 “⼀百幅⼩画”,三尚当代艺术中⼼ ;
2018年 “中央美术学院馆藏作品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廊坊馆,廊坊 ;
2017年 “⾦蝉脱壳-纪念⻩专逝世周年邀请展”,OCAT当代艺术中⼼,深圳 ;
2008年 迈阿密当代艺术展,迈阿密 ;
2007年 “回声与反响”,四⽅⼴场,纽约 ;
2007年 “观物”,中央美术学院 | 中国美术学院,北京 | 杭州 ;
2007年 “第⼀届亚洲当代艺术节”,纽约 ;
2007年 “预感......”,艺术⽅位,深圳 ;
2006年 “中央美术学院教学素描典藏”,北京 ;
2006年 “我们是幸福的牺牲品—张春阳、秦晋作品展”,OCAT当代艺术中⼼,深圳 ;
2005年 “学院—变异”,⻘年艺术沙⻰,上海 ;
2004年 “⽩⽯油纪—全国邀请展”,刘海粟美术馆,上海 ;
2004年 “国际交流展”,美国哥伦⽐亚⼤学,哥伦⽐亚。
免责声明:市场有风险,选择需谨慎!此文仅供参考,不作买卖依据。
文章投诉热线:156 0057 2229 投诉邮箱:29132 36@qq.com